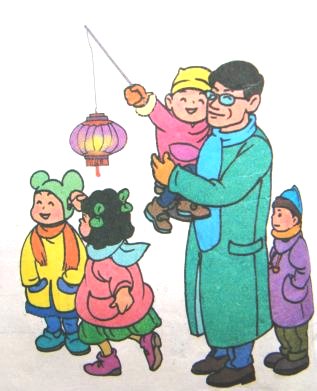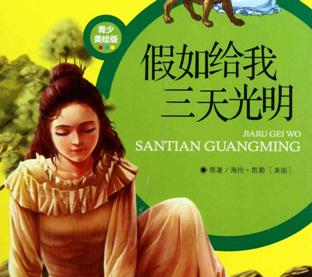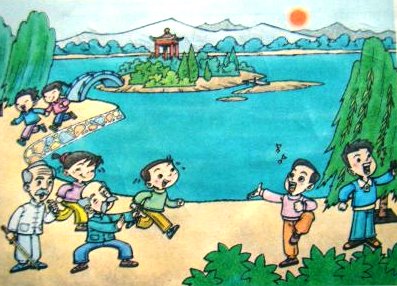春秋戰(zhàn)國典故集錦(7)
《戰(zhàn)國策》中的內(nèi)容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,但因作者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,有很多地方都顯得有一定的牽強,其可信性值得懷疑。《戰(zhàn)國策·齊策》也是如此,有很多可疑之處,以上的事件未必沒有添油加醋之嫌,具體的就不一一在此辨別了。
39.利令智昏
出自《史記·平原君虞卿列傳》司馬遷在文末的評述中說:“鄙諺曰:‘利令智昏。’平原君負馮亭邪說,使趙陷長平四十余萬眾,邯鄲幾亡。”
長平一戰(zhàn)之前,秦攻打韓,韓國的一部分土地與韓國本土失去了聯(lián)系,這一塊地就是上黨地區(qū),韓國便把它割讓給秦國,以求茍且。但是上黨的軍民痛恨秦國,他們在馮亭的帶領下要求向趙投降。
在趙國內(nèi)部,關于是否接受馮亭的投降起了爭議,一部分人認為,接受投降,必然引起秦國的惱怒,到時候,秦必定大舉來攻打,這是趙國不愿意看到的。以平原君趙勝為首的一部分人則主張,上黨地區(qū)是咽喉要地,且不費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,何樂而不為。
趙國最終接受了上黨的投降,并由此引發(fā)了戰(zhàn)國史上有名的“長平之戰(zhàn)”,戰(zhàn)爭的結果就不用說了,大家都知道。
40.兵不厭詐
出自《韓非子·難一》:“臣聞之,繁禮君子,不厭忠信;戰(zhàn)陣之間,不厭詐偽。”
春秋時期,齊國自齊桓公稱霸之后,因為后繼不力,退出了霸主地位。在整個中華大地,一個新的霸主呼之欲出。而楚、秦、晉都是有力的爭奪者。
這個時候,楚國與晉國的矛盾已經(jīng)不可調(diào)和。楚欲稱霸必須向北進,而晉又如何肯向楚國低頭。公元前633年。楚攻宋,宋雖然不失為一個二等強國,但也絕非是十七正盛的楚國的對手,宋向晉求救。
這個時候,晉國出了個公子重耳,他在王位的爭奪中敗下了陣來,無奈之余。晉國并未派出大軍與楚國正面交鋒,而是攻打了楚國的附庸國曹和衛(wèi)。楚國于是派并前來與晉決戰(zhàn),戰(zhàn)爭初期,楚占據(jù)上風,晉卻使用靈活的外交手段,使得秦齊皆助晉國。此時,楚成王見局勢對己不利,便下令撤退。但是楚軍主將子玉一心與晉決戰(zhàn),于是帶領部隊前來與晉軍交戰(zhàn)。
晉文公重耳當初爭奪王位失利,被迫離開晉國落難他國的時候,一些小國卻并不禮遇他,而楚王卻給了盛情款待了他。楚王問重耳,如果他日你當上晉國國君,如何報答我?重耳恭敬的回答:如晉楚國之間發(fā)生戰(zhàn)爭,我命令軍隊先退避三舍(這個成語出于此時),再與您交戰(zhàn)。
晉國面隊來勢洶洶的楚軍,就主動的退后了三舍的距離,到達城濮。晉軍的主動后退起到了誘敵深入(這個詞的典故應該是出自于毛澤東,而不是戰(zhàn)國時期)的目的,也履行了當初重耳的諾言,可謂一石二鳥,得了便宜還賣了乖。
最終,晉在城濮大勝了楚軍,戰(zhàn)爭的過程就不必講了,大家都清楚。楚國完敗,子玉繼承了楚軍主將在戰(zhàn)敗后自殺的傳統(tǒng),但也不能用“慘”字來形容楚國,畢竟楚軍主力還在,并未太多的傷及筋骨。這一戰(zhàn)確立了晉的霸主地位,楚國也并未完全退出霸主的爭奪,但秦晉在此一段時間內(nèi)成為爭霸的主角。
兵不厭詐”近乎完美的表現(xiàn)在了整個大戰(zhàn)過程中,這也是晉國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,也是“詐”的最完美最忠實的執(zhí)行者,秦楚等國常常是其玩弄的對象,例如趙盾先迎秦軍,以立襄公弟,后反悔,不迎接不說,反而派并攻打護送的秦軍。晉之后,秦國人優(yōu)良的學習傳統(tǒng)得到了發(fā)揮,也在“詐”字下了不少功夫,比如和氏壁、騙楚王入秦扣押等等,可謂學有所成;而楚國在“詐”字上自然比不上前兩位了,吃虧當然也就是不計其數(shù)了。
41.馬首是瞻
出自于:《左傳·襄公十四年》:荀偃令曰:“雞鳴而駕,塞井夷灶,唯余馬首是瞻!”
春秋時期,晉國作為中原大國,處于天下的政治中心和地理中心,其他大國如要稱霸,必須要過晉國這一關,反之,如果晉國要確立其霸主地位,也必須擊敗其他的挑戰(zhàn)者。所以,秦、楚都與晉國發(fā)生過多次的大規(guī)模戰(zhàn)爭,總的來說,各有勝負,任何一方都沒有確立絕對的優(yōu)勢。